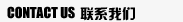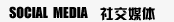關于星巴克的“壞新聞”在經濟學常識上的欠缺,在諸多科普之下,現在已不必多言。但是,仍然存在一些不同意見。
比如,有人認為——一杯咖啡,非要喝出點情調來,并由此產生文化與身份認同,反映了大眾的媚外心理,所以,媒體有責任提醒公眾,并打破這種文化上的集體無意識。還有人認為,價格歧視的原因在與市場分割,而市場分割背后則是信息不對稱,所以,媒體的報道實際上打破了這種信息不對稱,有利于促進一個更加公平的價格。
這些看法粗看有一些道理,但是,如果仔細推敲,就會發現其中的問題。
按照馬斯洛需求層次,人有“尊重需求(Esteem needs)”,如:成就、名聲、地位等。這些需求往往又物化為一些具體事物,從鮮衣怒馬,到LV寶馬,變的是物品,不變的是人性。至于哪些物品能充當這個符號,除了價格之外,有時候也源于強勢文化,而強勢文化的根源則是技術、經濟、社會的領先優勢。從這一點上來看,西方文化在輸出技術的同時輸出奢侈品,并不奇怪。某種程度上看,這不過是“師夷之長技以制夷”過程的一種必然衍生效應。
在這個輸出強勢文化的趨勢中,星巴克不過是其中一個較為低端的符號,迅速的由最初的虛榮,變成下意識的求同,成為某個群體的日常品。但無論如何,在一個人均年收入2萬多元的國家,30元一杯的咖啡必然是一種消費升級,而消費升級則必然會連帶出身份感。
值得一提的是,雖然一些人瞧不上星巴克,認為其完全不足以支撐所謂的“身份感”,但有趣的是,就連這種鄙視“喝星巴克裝小資”的行為,本身也是一種逆向的“裝”,本質上仍是以此顯示更高的品位,彰顯身份優越,比如:“星巴克完全是快餐檔次,我鐘意的是意大利咖啡。”
所以,圍繞星巴克所產生的身份認同,看似虛無縹緲,實則根深蒂固,是貫穿于人類社會的一種不可避免的合理現象。
至于打破信息不對稱的說法,應該說,媒體比較各國同一商品的價格,并不為過。實際上,此次媒體引用的調查也是華爾街日報所做。根據該調查顯示,今年2月份全球29個城市大杯拿鐵的價格,北京在29個城市中,價格排名第11位。比北京更貴的城市有奧斯陸、斯德哥爾摩、莫斯科、雅典、法蘭克福、巴黎和悉尼等。而最便宜的5個地方是:新德里、墨西哥城、舊金山、底特律和倫敦。最貴的奧斯陸(9.83美元)比最便宜的新德里(2.80美元)貴了好幾倍。
不同于華爾街日報詳細列舉了成本的構成,國內一些媒體,不但只列出了比北京便宜的城市,而且在解釋成本構成的時候,還把公眾的注意力引向物料成本,故意忽略租金、人力、運營費用、稅費、翻臺率。
媒體還引用的上海市咖啡專業委員會會長王振東的說法,稱星巴克應按當地收入定價,合適的價格是10元。實際上,王振東是上海甜魔的公司與君客飲品技術培訓中心的老板,旗下有幾家咖啡店。而上海市咖啡專業委員會,也僅有包括甜魔公司在內的十幾個會員,公眾比較熟悉的星巴克、COSTA、太平洋、SPR、上島、雕刻時光都不是其會員。所以,毫不奇怪的,這個協會的聯系地址與郵箱和王振東公司的聯系方式一模一樣。
媒體應當做到公正,對事實的解釋也應該專業、合理,不誤導公眾,而事實卻恰好相反。所以,所謂信息不對稱,本身就是個偽問題,媒體的報道與其說打破了信息不對稱,不如說制造了信息不對稱。
如果說以上兩個觀點僅僅是受到誤導之后,出于樸素的、直觀的感受,未能認識到其背后的邏輯與必然性,僅僅是知識之爭的話,那么,另一些論調則更需警惕。
比如,有媒體評論認為,央視報道星巴克價格問題,“其報道方向符合中國消費者的利益”,而批評央視的報道,則是“犧牲中國公眾的利益”;如果“星巴克在中國賣的不是咖啡,而是服務,而麥當勞和肯德基又何嘗不是同時賣了服務呢?”
應該說這種觀念很有市場,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鳴,但這種說法似是而非,可以毫不夸張的說,把孔子所謂的“言偽而辯,順非而澤”做到了極致。餐飲業在提供產品的時候,必然也需要提供服務,但沙縣小吃賣的服務能與海底撈比嗎?更遑論五星級酒店的高檔餐廳所提供的服務?
更重要的是,這種觀點贊同媒體壓制商家,表面上是以老百姓利益為重,但一個真正能保護商家合法利益,不用民粹去壓制商家利潤的社會,才是中國經濟,中國創新,中國老百姓的長遠利益之所在。
其實,這樣的歷史已經發生過了。現在網上流傳著這樣一個段子,某官員訓斥抗爭征地的農民時說:“征你的土地,一畝地還給你3萬塊錢,不錯了!想當年你的土地是從地主手里搶來的,一分錢沒給,還把人家斗死了呢!還瞎鬧個啥?”
太陽之下無新事,所以,當今天星巴克面對輿論的批斗時,為之說話,不僅是因為星巴克本身,更是因為厭惡其中的手法,反對其中的邏輯,害怕這種邏輯導向的現實后果,最終,是為現在的,以后的我們說話。
本文資料來自“壞新聞”,特此致謝。
關于星巴克的“壞新聞”在經濟學常識上的欠缺,在諸多科普之下,現在已不必多言。但是,仍然存在一些不同意見。
比如,有人認為——一杯咖啡,非要喝出點情調來,并由此產生文化與身份認同,反映了大眾的媚外心理,所以,媒體有責任提醒公眾,并打破這種文化上的集體無意識。還有人認為,價格歧視的原因在與市場分割,而市場分割背后則是信息不對稱,所以,媒體的報道實際上打破了這種信息不對稱,有利于促進一個更加公平的價格。
這些看法粗看有一些道理,但是,如果仔細推敲,就會發現其中的問題。
按照馬斯洛需求層次,人有“尊重需求(Esteem needs)”,如:成就、名聲、地位等。這些需求往往又物化為一些具體事物,從鮮衣怒馬,到LV寶馬,變的是物品,不變的是人性。至于哪些物品能充當這個符號,除了價格之外,有時候也源于強勢文化,而強勢文化的根源則是技術、經濟、社會的領先優勢。從這一點上來看,西方文化在輸出技術的同時輸出奢侈品,并不奇怪。某種程度上看,這不過是“師夷之長技以制夷”過程的一種必然衍生效應。
在這個輸出強勢文化的趨勢中,星巴克不過是其中一個較為低端的符號,迅速的由最初的虛榮,變成下意識的求同,成為某個群體的日常品。但無論如何,在一個人均年收入2萬多元的國家,30元一杯的咖啡必然是一種消費升級,而消費升級則必然會連帶出身份感。
值得一提的是,雖然一些人瞧不上星巴克,認為其完全不足以支撐所謂的“身份感”,但有趣的是,就連這種鄙視“喝星巴克裝小資”的行為,本身也是一種逆向的“裝”,本質上仍是以此顯示更高的品位,彰顯身份優越,比如:“星巴克完全是快餐檔次,我鐘意的是意大利咖啡。”
所以,圍繞星巴克所產生的身份認同,看似虛無縹緲,實則根深蒂固,是貫穿于人類社會的一種不可避免的合理現象。
至于打破信息不對稱的說法,應該說,媒體比較各國同一商品的價格,并不為過。實際上,此次媒體引用的調查也是華爾街日報所做。根據該調查顯示,今年2月份全球29個城市大杯拿鐵的價格,北京在29個城市中,價格排名第11位。比北京更貴的城市有奧斯陸、斯德哥爾摩、莫斯科、雅典、法蘭克福、巴黎和悉尼等。而最便宜的5個地方是:新德里、墨西哥城、舊金山、底特律和倫敦。最貴的奧斯陸(9.83美元)比最便宜的新德里(2.80美元)貴了好幾倍。
不同于華爾街日報詳細列舉了成本的構成,國內一些媒體,不但只列出了比北京便宜的城市,而且在解釋成本構成的時候,還把公眾的注意力引向物料成本,故意忽略租金、人力、運營費用、稅費、翻臺率。
媒體還引用的上海市咖啡專業委員會會長王振東的說法,稱星巴克應按當地收入定價,合適的價格是10元。實際上,王振東是上海甜魔的公司與君客飲品技術培訓中心的老板,旗下有幾家咖啡店。而上海市咖啡專業委員會,也僅有包括甜魔公司在內的十幾個會員,公眾比較熟悉的星巴克、COSTA、太平洋、SPR、上島、雕刻時光都不是其會員。所以,毫不奇怪的,這個協會的聯系地址與郵箱和王振東公司的聯系方式一模一樣。
媒體應當做到公正,對事實的解釋也應該專業、合理,不誤導公眾,而事實卻恰好相反。所以,所謂信息不對稱,本身就是個偽問題,媒體的報道與其說打破了信息不對稱,不如說制造了信息不對稱。
如果說以上兩個觀點僅僅是受到誤導之后,出于樸素的、直觀的感受,未能認識到其背后的邏輯與必然性,僅僅是知識之爭的話,那么,另一些論調則更需警惕。
比如,有媒體評論認為,央視報道星巴克價格問題,“其報道方向符合中國消費者的利益”,而批評央視的報道,則是“犧牲中國公眾的利益”;如果“星巴克在中國賣的不是咖啡,而是服務,而麥當勞和肯德基又何嘗不是同時賣了服務呢?”
應該說這種觀念很有市場,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鳴,但這種說法似是而非,可以毫不夸張的說,把孔子所謂的“言偽而辯,順非而澤”做到了極致。餐飲業在提供產品的時候,必然也需要提供服務,但沙縣小吃賣的服務能與海底撈比嗎?更遑論五星級酒店的高檔餐廳所提供的服務?
更重要的是,這種觀點贊同媒體壓制商家,表面上是以老百姓利益為重,但一個真正能保護商家合法利益,不用民粹去壓制商家利潤的社會,才是中國經濟,中國創新,中國老百姓的長遠利益之所在。
其實,這樣的歷史已經發生過了。現在網上流傳著這樣一個段子,某官員訓斥抗爭征地的農民時說:“征你的土地,一畝地還給你3萬塊錢,不錯了!想當年你的土地是從地主手里搶來的,一分錢沒給,還把人家斗死了呢!還瞎鬧個啥?”
太陽之下無新事,所以,當今天星巴克面對輿論的批斗時,為之說話,不僅是因為星巴克本身,更是因為厭惡其中的手法,反對其中的邏輯,害怕這種邏輯導向的現實后果,最終,是為現在的,以后的我們說話。
本文資料來自“壞新聞”,特此致謝。